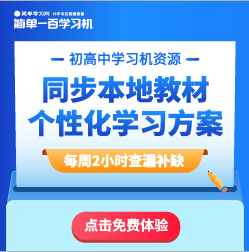意境是我国文艺审美的重要准则。“意境”一词出自唐代王昌龄的《诗格》:“诗有三境:一曰物境,二曰情境,三曰意境……意境三:亦张之于意而思之于心,则得其真矣。”笔者以为,意境作为一种审美体验,是作者和读者在对话中形成的场域。从接受美学来看,作者用意象把读者引向意境的营造。学者宗白华认为:“艺术的意境因人因地因情因景的不同,现出种种色相,如摩尼珠,幻出多样的美。”意境在读者接受中呈现千人千面的特点,但意境的营造不是读者主观臆断的呓语,不是随意想象、任意发挥的,而是基于文化背景的同频、文化底蕴的积淀形成的审美共振。
意象是营造意境的基础。《周易》中提出“立象以尽意”,但没有将“意”与“象”结合起来。南朝刘勰在《文心雕龙·神思》中写的“窥意象而运斤”,最早用“意象”一词。意象在有与无、实与虚、彼与此、显与隐之间搭建起超越的桥梁。古代有很多用简单的意象营造出超凡脱俗意境的诗句。例如,南朝谢灵运的《登池上楼》中一句“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在我国诗歌史上达到了让人难以企及的高度,受到历代诗人的追捧。唐代李白在《赠从弟南平太守之遥二首》中有“梦得池塘生春草,使我长价登楼诗”,宋代朱熹在《劝学诗》中有“未觉池塘春草梦,阶前梧叶已秋声”,元代元好问在《论诗三十首》中也有“池塘春草谢家春,万古千秋五字新”的赞叹。
意象是审美的积淀,通过意味、意蕴呈现意境,也就是宋代严羽在《沧浪诗话》中提出的“言有尽而意无穷”。这在很多诗论中有所体现。例如,唐代刘禹锡的《董氏武陵集纪》中有“境生于象外”,宋代姜夔的《白石道人诗说》中有“句中有余味,篇中有余意,善之善者也”,明代袁中道的《淡成集序》中有“天下之文,莫妙于言有尽而意无穷,其次则能言其意之所欲言”……可以看出,诸多文艺评论家主张基于意象来寻求象外之意,“境”正在味中,是从味中品出来的、悟出来的。
意象的选取对意境的营造是有影响的。唐代皎然在《诗式》中提出:“诗人诗思初发,取境偏高,则一首举体便高,取境偏逸,则一首举体便逸。”宋代苏东坡在《题渊明饮酒诗后》中提出:“‘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因采菊而见山,境与意会,此句最有妙处。近岁俗本皆作‘望南山’,则此一篇神气都索然矣。古人用意深微而俗士率然妄以意改,此最可疾。”近代俞陛云评唐代杜甫的《江南逢李龟年》:“余味深长,神韵独绝,虽王之涣黄河远上,刘禹锡潮打空城,群推绝唱者,不能过是……此诗以多少盛衰之感,千万语无从说起,皆于‘又逢君’三字之中,蕴无穷酸泪。”跟元代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类似的则有白朴的《天净沙·春》:“春山暖日和风,阑干楼阁帘栊,杨柳秋千院中。啼莺舞燕,小桥流水飞红。”这个有山、有楼、有柳、有桥、有水的地方,组成了很多人或熟悉或向往的生活场景,不管听到、看到还是读到,在蕴藉无穷的共鸣、共振、共情中自然会有意境的生成。
意境的理论阐释是逐步演变成熟的,在学者王国维的《人间词话》中实现了古今与中外的汇通。王国维提出:“惜(姜夔)不于意境上用力,故不觉言外之味,弦外之响,终不能与于第一流之作者也。”在这里,意境已经是王国维评判古今词人的最高标准。假托山阴樊志厚所写的《〈人间词〉序》中也称:“文学之事,其内足以摅己,而外足以感人者,意与境二者而已。上焉者意与境浑,其次或以境胜,或以意胜。苟缺其一,不足以言文学。”由此可见,意象的简单罗列并不能营造意境,而需要情景交融浸染情感的描摹。明代王夫之在《姜斋诗话》中就曾提出:“情、景名为二,而实不可离。神于诗者,妙合无垠。巧者则有情中景,景中情。”
综上所述,意境基于意象又超越意象,基于现实又超越现实,在对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我的思考中呈现出审美追求,在精神的高蹈中实现审美的升华,并引起读者的思考和共鸣,文艺作品“澡雪精神”的作用由此得到体现。值得一提的是,我国文艺作品中的意象有自身的特色,例如月、云、梅、松、雪、笛、蝉、雁等意味无穷,所积淀成的文化底蕴已经成为今天人们进行交流的“文化密码”。
(来源:《中国文化报》2024年12月30日,第3版;作者:党云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