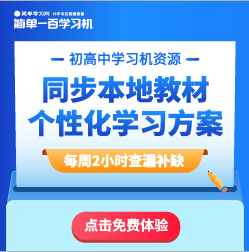引子
#本文摘自《从革命女志士到头号女汉奸——陈璧君传记》张静星著(1994年5月),原节标题《覆巢之下无完卵 大小汉奸纷落网 通敌谋国罪不容 死党诀别暗神伤》

1945年8月10日,日本宣布投降,陈璧君听到这个消息目瞪口呆,如丧考妣。尽管她已知道末日即将来临,但真到了这一天,仍然免不了十分沮丧。今后怎么办?陈璧君的侄子和一些亲信听到这个消息,纷纷逃往香港,其他汉奸一个个惶惶不可终日。陈璧君却故作镇静地对他们说:“不用慌!我们的目的是求和平,现在这个目的已达到,我们的任务完成了。在这个时候,是汉奸才用得着发慌,我们又不是汉奸,慌什么呢?”她命褚民谊给重庆去电进行试探,并要褚向国民政府新委任的广东省主席罗卓英表示,坚决遵守蒋介石的训示,等候接收。
8月15日,日本天皇正式下诏无条件投降。16日,陈公博打电话给陈璧君,告知日本方面表示,如她愿意赴日本或其他国家,日本将派飞机来接。同一天,日本军部也正式派人通知褚民谊和陈璧君,如愿意离开,飞机轮船均可代为准备,如不走,则拟拨日军百人来守卫陈璧君和褚民谊两人的住宅。大势已去,逃走他国显然是作贼心虚,尽管陈璧君内心十分恐惧,但她向来是个不肯认输的女人,她要为汪精卫、为自己辩解,她还有侥幸的心理。让日军来守卫自己的住宅,更是不合时宜,这岂不是往自己脸上贴汉奸的标签?陈璧君和褚民谊商讨后表示哪里都不去,也不要日本兵来守卫。陈璧君还故作姿态,与褚民谊一起外出巡行,美其名曰“安定人心”,实质是探听虚实。
日本投降后,重庆当局很快电令汪伪海军部次长招桂章为广州先遣军司令。招原为汪伪广东省海军司令,因对陈璧君不是言听计从,被她用明升暗降的手法逐出广东,在南京伪政府中当挂名的海军部次长。如今招桂章以先遣军司令的身份重返广州,陈壁君当然不便求他帮助,唯有整天躲在家中,催促褚民谊等抓紧与重庆联络,陈璧君还和褚民谊一起打电报给蒋介石,表面上声称“罪只在我辈,中下级工作人员请从宽处理,妥善安排”。但是当陈璧君一向视为左右手的广东教育厅长林汝珩、警务处长汪屹等在日本投降后失去踪迹,其他亲信也相继失踪时,陈璧君大骂林、汪两人“无良心”、“无阴功”、欺凌她是寡妇等等,其实这几个人已被国民党当局拘捕。
8月下旬,国民党军统局华南特工主任郑介民和翟荣基两人来到陈璧君寓所求见,提出请陈璧君、褚民谊两人暂时避开,否则恐民愤对他们不利,并说这是蒋委员长关怀两位的安全,说着出示了一份电报。但陈璧君态度十分坚决,她表示“待罪家中为最宜的事”。过了几日,郑介民手持重庆方面的电报交褚民谊过目,电报全文如下:重行兄(褚民谊字重行):兄于举国抗战之际,附逆通敌,罪有应得。惟念兄奔走革命多年,自当从轻以处。现已取得最后胜利,关于善后事宜,切望能与汪夫人各带秘书一人,来渝商谈。此间巳备有专机,不日飞穗相接。弟蒋中正①
电报上还附有密码,丝毫不像是伪造的。郑介民还讲他得到重庆另一电文,知专机后日即可抵穗,望他即转告汪夫人早为准备,同时告知可带随从两人,行李少带。处于惶惶不可终日的褚民谊见此情景,毫不怀疑。
陈璧君在广州的住宅与褚寓隔街相望,亦在法政路。郑介民一走,褚民谊立即去见陈璧君,告知这一消息,要她早做准备。
“这也许是一个圈套,如果真是蒋介石的意思,决不会有行李少带的话。”陈璧君半信半疑,沉吟着说。
“时至今日,管他真假,事关中下级人员安危,龙潭虎穴也当一行。”褚民谊苦笑着说,“我们若是不去,委员长会说我们没有诚意而兴问罪之师,届时我们更加被动了。”如果说为所谓中下级人员的安危而行可作为一条理由的话,那么褚民谊的后一句话更道出了他的真实想法:如果拒绝蒋介石的“邀请”岂不断了自己的后路?
“我也在考虑这一点。”陈璧君表示同意褚民谊的看法,她似乎下了决心,“我是应该去重庆走一趟,那儿的不少朋友对汪先生的和平运动有误解,有必要向他们作些解释,使他们明了真相,明了汪先生的良苦用心。至于个人荣辱安危,用不到多顾忌了。”其实陈璧君的疑窦丛生、举棋不定,正是担心自身的祸福,但此时她仍抱有侥幸心理。所以末了又补充一句,“但愿老蒋言必信,行必果,以诚待诚,捐弃前嫌,不要做得太绝。”
“蒋委员长与汪先生都是为救国,属殊途同归,且又都是总理的忠实信徒,曾共事多年,谅会念及旧情的。”褚民谊与其说是在宽慰陈璧君,不如说在宽慰他自己。
陈璧君忙着收拾行装。她的秘书拿了汪伪政府委任陈璧君为粤省政治指导员的特派状说:“如果您舍不得它,要留作您的纪念,我便立即拿出外存,不然就烧了它。“
“为什么?“
“您如果无这个特派状,您只是一个家属,有了这个,您就要负责任的。”
陈璧君很动情地说:“我不能因我的‘卸责’而让汪先生有纵妻干政之名。您可将这特派状摆在汪先生灵前,让他们入室便看见。”
“这样,您会受死刑的。”秘书恳切地说。
“事实如此,不要因救生人而冤在死人。”陈璧君对汪精卫可谓是忠心耿耿,在这一点上,她从来是不含糊的。无论是在蒋介石政府的法庭上,还是在人民政府的监狱中,每当涉及到汪精卫,陈璧君总是竭力为汪精卫辩护。
9月12日黎明,陈璧君、褚民谊等人随郑介民和全身美式装备的翟荣基出发了。郑介民调来了十余辆汽车,宣布每车只准乘坐两人,其余座位由军统陪送人员乘坐。按常例,从广州至重庆的飞机都在白云机场起飞,而陈璧君等人乘坐的汽车却向珠江方向疾驶而去。
“等一等,郑先生,这是去哪里?”陈璧君发现方向不对,惊异地问,“怎么不去白云机场?”
郑介民欠了欠身体,平静地说:“噢,刚才忘了告诉汪夫人,重庆来的是美制水上飞机,所以要到珠江上船过渡。”
在珠江大桥附近,已有两艘小汽船在码头上等候,陈璧君等相继上船后,郑介民说:“兄弟还有公务留穗,由何先生陪你们去重庆。”说着指了指一位佩戴中校军衔的军官,随即上岸,钻进汽车走了。
汽船离开码头后不久,何中校点头为礼道:“汪夫人、褚先生,重庆方面来电:蒋委员长现正因公留成都,四五日内不能回渝,陈璧君等一行此时来渝,殊多不便,请先送至安全地区,妥为保护。”说着取出一份电报在手中扬了扬。随即又宣布为确保旅途安全,飞机上不能带武器,如有武器应立即交出。
“我们谁也没带武器。”陈璧君抢先回答。她看了看褚民谊,明白事情不妙,郑介民所说的一切都是预先做好的圈套。陈璧君站起来拍着桌子高叫,“既是老蒋不在重庆,我就没有去的必要。若论安全,我自己的家里,才是最安全的地方。不必麻烦你们了,赶快靠岸,送我们回家!”
见这位背日的贵夫人发怒,负责监送的何中校板起面孔道:“去哪里,上峰已作安排,不能随夫人所欲。”
“我自己的事,用不到你们安排。”
“我们是奉上司的命令办事,请夫人原谅。”何中校的口气缓和了些。
“谁的命令我不管,只要你让我回家。”陈璧君的声音越来越大。
褚民谊见事已至此,争执也无济于事,便也帮同劝说,要她暂时忍耐一下,以待事态进一步变化。经众人劝说,陈璧君虽不再坚持开回原处,但一路上仍大吵大骂。
汽船开到市桥,那位军统负责人又要他们改乘小船,陈璧君怒气更盛,扶着栏杆厉声说:“我央不下小船去再听你们的摆布,除非你们用枪打死我。“
随船的军统特工一齐端起手提机枪,从四面环视着她,形势顿时变得十分紧张。陈璧君毫不退让,还像平时一样以训斥的口吻,瞪着眼睛说:“老蒋都知道我的脾气,你们是什么东西,敢这样对我?”双方相持不下,一时形成僵局。
褚民谊知道越闹对自己的处境越不利,于是又向陈璧君劝说:“与他们争吵毫无作用,假使重庆方面决意和我们过不去,我们也没有办法,只能听天由命。夫人还是过去吧,免得何先生他们为难,再说自己家里也不一定安全。”说着便先自下了小汽艇。
陈璧君觉得褚民谊说的也在理,勉强上了小船。不一会儿,小船开进了一条河。上岸后,只见一幢楼房,四面临水,这里原是伪师长李辅群夏天用以避暑的地方,有时抓到“肉票”。也关在这里。现在这幢房子已为国民党特工所接管。李宅是一所两层楼的房屋,在空旷的院子里,有十余个士兵携着卡宾枪守卫。陈璧君刚进门就听到一个很熟悉的声音,是原伪广东省财政厅长汪宗准的说话声,随即又听到另两个厅长的回答声。陈璧君恍然大悟,原来前不久“失踪”的几个厅长已比她先到一步,这会儿的陈璧君只有哀叹的份儿了。
日本宣布投降后,重庆国民政府开始逮捕汉奸。戴笠接到蒋介石逮捕陈璧君的指令后,因知道她秉性傲而悍,操之过急,可能会狗急跳墙,以武力抗拒,便与郑介民等周密策划制订了一套诱捕方案。陈璧君虽然狡猾,因求生心切,身不由己地堕入圈套。
陈璧君、褚民谊等被带上二楼,指定两人各住一个房间。陈璧君与女佣住在一块。看守人员告诉他们,除了不准下楼外,可以自由行动。如需要饮食用品,可通知他们办理。每人床上蚊帐、毛毯等也一应齐备。陈璧君因生肺炎原有些发烧、咳嗽,因此进房后便倒床休息。
生活虽算可以,但前途未卜,每个人的心里都忐忑不安,每天唯以下棋、看书来消磨难熬的时光。陈璧君对抗战胜利后的时局十分关注,每天的报纸她都仔仔细细地从头到尾看个够。当她从报纸上了解到张发奎已回到广东省时哀叹道,“真是一场梦啊!”想到自己苦心经营的地盘已不复存在,一种凄凉的失落感油然而生。
一个多星期过去了,陈璧君见仍没有什么动静,便找到看守主任,怒气冲冲地说:“我磊落光明,坐家候捕,死亦应死于明处,不赴重庆,便当送我回广州,枪决亦应在民众面前,不能失踪,况且你们尚可抢劫广州后,诬我们潜逃,如不送我回去,我从今日起便绝食。”陈璧君果然两天未进食。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的接收大员们借接收之机大肆“劫收”,搞得民怨沸腾,因此陈璧君的担心也不是没有道理的。晚年,她在《自白书》上亦提到当年的情况,但字里行间流露的并不是对国民党“劫收”的痛恨,而是借以反衬自己,开脱自己罪责的表白。她这样写道:“知张发奎已回省,闻十数日后搭牌楼欢迎彼等时,牌楼上有对联写‘抗战八年容易过,和平十日实难’语,则彼等骄奢暴掠亦可知矣。‘重庆人’几乎比美‘天上人’,又有五子登科之谣,即车子、房子、窑子、馆子、金子,闻上海亦有此等说法。”
9月下旬,陈璧君等人被押送回广州。他们每人被送进一辆汽车,两面有武装士兵挟持。陈璧君等人在广州的幽囚之处就在她的原住宅附近,曾是一个日本军官的住所。在那里。他们一人一室,陈璧君和褚民谊及一些随从住楼上,四个厅长住楼下。这里的条件已远非市桥时的情形可比,住室条件和伙食等都比原来的差,只是表面上还不是监狱的样子。陈璧君自8月份感染了肺炎后一直未痊愈,再加上心情烦闷,身体很虚弱,除肺炎外,又肠出血不止,国民党当局允许原给她治病的医生为她诊治,经过一段时间的用药治疗后,身体稍有恢复。
在广州拘押两周后的一天,军统局一个姓徐的军官来到陈璧君的房间。
“上面已来了命令,汪夫人等日内将被送去南京。”这个军官说。
“去南京解决?”陈璧君愁容满面。“我有受死的勇气,但决无坐牢的耐性。三尺斗室,终年不见天日,如何吃熬得过?”
“估计会用政治手段解决,不会送司法审判的。汪夫人不必多所顾虑,为时也不会太久的。”或许是真不知内情,这个军官说了一番宽慰的话。
“假若真的不交司法审判,就谢天谢地了。”陈璧君双手合十,默默地祈祷“上帝保佑”。
11月初,军统人员先把各人身边的贵重物品,包括手表、钢笔等全部收缴。14日下午,一架美国军用飞机从广州白云机场升空,把陈璧君、褚民谊及伪广东省四个汉奸厅长解往南京。她的长女汪文惺等五人一同前往。
到南京,陈璧君等被关押在宁海路21号。几天后,陈公博等人也被押送到这里。看守所长徐文祺,是汪伪政权中的旧人,曾任行政院庶务科长之职,这时已摇身一变,成为国民党政府看守汪伪政权要犯的所长了。
当时被关押的汉奸每人都被要求写坦白书,看守人员叫陈璧君也写。陈璧君回答说:“我不必写,如要写,你们代写,由我签署可以,我病甚倦,不必扰我。”看守人员见其态度蛮横,也无可奈何,此后竟也无人叫她写坦白书了。
由于生活清苦,心境不佳,陈璧君的身体一直不太好,到南京后,她的三女儿特意为她请来医生医治,陈璧君在南京的长子汪文婴也特意入狱陪侍。对此,陈璧君描述说:“我长子在南京未被逮捕,但这‘愚孝’的儿子知我已来,且病重,便自行到何应钦处请求逮捕入侍母疾。他来了,与弟、妹、甥、妹夫、表弟等都团聚了。特工所长安置他在我的隔房,便于他的侍疾。”②
国民党方面因陈璧君是要犯,身份特殊,又未经审判,只是暂时拘押,所以给予她特别优待。陈璧君足不出门,一直呆在房间里或看书,或静坐,有事喊儿子、女儿,随叫随到。看守所内规定每天有半个小时自由活动,子女劝她去院子里散散步,做做操,以免憋出病来,她也一概拒绝。室内的清洁工作,由其子女轮流负责,稍有不如意,陈璧君便大呼小叫,甚至呵斥,他们也都惟命是听,不说半个“不”字。
一次,一位看守在例行检查时直呼其名,她立即慎目怒斥:“陈璧君这个名字是你叫的吗?当年国父孙先生不曾这样叫过我,你们委员长不敢这样叫我,你是国民党下面雇佣的人,你配这样叫我?”说也奇怪,从此看守人员再也不敢对她直呼其名了,每次传呼,不是称她“汪夫人”,就叫她“陈先生”。
一日,陕西省警备司令部某稽查处处长前来南京公干,听说陈璧君也收押宁海路看守所,因先前只闻其鼎鼎大名,不识其何等模样,出于好奇,经请示军事委员会批准,以来看守所参观为名,想认识一下这个大人物。他身穿笔挺呢质军服,佩着少将军衔,在警卫簇拥下,步入看守所,随着有节奏的皮鞋声,蹬上了二楼。
“陈璧君关在什么地方?叫她出来。”那处长人未到而声先至。
陈璧君正躺在床上,忽听得有人高声叫她的名字,且是明显的轻视口吻,自尊心大挫,气得脸都歪了。她从房间里踱将出来,强压住满脸怒火,先抑后发,慢悠悠地问道:“什么人喊我?有什么事啊?我就是陈璧君。”
陪同稽查处长上楼的看守所长徐文祺,在该处长直呼陈璧君时,便暗叫“不妙”,却又不便劝阻,及至陈壁君出现在门口,觑见其眉宇间隐现的怒容,情知一场闹剧不可避免,但他仍力图挽救,忙抢前一步,微微向陈璧君一鞠躬:“汪夫人,这位是陕西警备司令部来的徐处长,想见见夫人。“
“何事要见我?去哪里谈?”陈璧君僵直脖子,一眼不眨盯着这位处长大人。
稽查处长也曾听说陈璧君性情傲岸,又见徐文祺对她如此恭敬,感到刚才过于唐突,忙摘下军帽,立正鞠躬说:“实际上也没什么事,只是想认识一下汪夫人。“
见对方卑躬,陈璧君越发气盛,雷霆大发:“你凭什么直呼老娘的大名?你们蒋委员长见了我,也要颔首致礼,称我一声‘汪夫人’。一个小小的处长,敢这样对待我?一介武夫,不知礼貌,你没有资格和我讲话。”说罢倏地转身进了房间,顺手把门用力一推,砰然作响。
处长大人遭到训斥奚落,满脸尴尬,如木鸡呆立,原本想观各所牢房,如今兴致一扫而光,沮丧下楼去了。
就在当天,徐文棋去军事委员会汇报了此事,请求今后不再准许外人参观看守所,以免触怒陈璧君,影响其身心,使对她的法律程序难以顺利进行。自后,果然无人再去参观,即便是军统局长戴笠巡视看守所时,对陈璧君也是避而不见。
陈璧君原是国民党的元老,对蒋介石的一套有比较多的了解,特别是对抗战期间蒋介石与日本暗中勾通的事实更是了如指掌,因而对汪精卫及自己甘心充当汉奸的卖国罪行不以为然,虽然身在囹圄,傲慢倔强之态度始终未改,但是陈君也自感与蒋介石结怨甚深,恐难逃一死,因而终日惶恐不安。
一天,徐文祺直入陈璧君房间,告诉她:“明天上午,汪夫人与褚先生要离开这里,请您准备一下。”
“去哪里?”她蓦的一惊,迫不及待地问。
“去苏州江苏高等法院,听说将要对汪夫人开庭审究。“
徐文祺说完,匆匆走了出去。
“审不审还不是一样?大不了枪毙!”陈璧君从鼻子里哼了一声。
1946年2月17日深夜,国民党军统局将陈公博、陈璧君、褚民谊三个重犯从南京解送苏州司前街看守所。不久,陈璧君被江苏省高等法院提起公诉,经过公开审讯,判处无期徒刑。陈公博、褚民谊均被判处死刑。
1949年6月2日,陈璧君和陈公博、褚民谊等重犯被移往苏州狮子口江苏第三监狱,6月3日,陈公博被枪决,行刑前,陈公博取了一把自己用的茶壶,来到陈璧君的羁囚之处,送给她留作纪念,并向陈璧君鞠躬告别说:“我先随汪先生去了。”陈璧君失声大哭,对陈公博说:“见了孙先生、汪先生,说我就来了。“
陈璧君在服刑期间,拒不认罪,她的强烈的不服输的个性丝毫未变,动辄吵闹,以绝食相威胁,狱方对她毫无办法,为防止出什么意外,故而多所迁就。
8月23日,是褚民谊被枪决的日子。褚民谊来到女牢前与陈璧君告别:“夫人,来生再会。”他本想装出一点笑容,却比哭还难看。陈璧君怔怔而视,未作一言。法警将褚民谊架走了,陈璧君还呆呆立着。“夫人,我去了……”褚民谊转过头来,绝望地喊了一声。陈璧君重重地跌坐在床上,以手帕掩面,哀哀抽泣起来。以后一段时间,时常有一些汉奸被枪决,陈璧君感到“良友渐随千劫尽矣”。为了摆脱可怕的孤独感,消磨难熬的时光,陈璧君夜间回女监休息,清早便到礼字监读书写字,为监狱印刷厂做些校对工作。她的身体状况已大不如前了,牙齿摇动,双眼昏朦,两耳失聪。心脏病、肝病、腰痛、头晕等时有发作。有一段时间,两只脚也不能行走,狱方只能安排人拾她。陈璧君的一些故旧老友曾设法将她保释就医,但未成功。
1949年春,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后,国民党军队精锐丧失殆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饮马长江北岸,随时准备打到南京去。国民党统治集团一片混乱,惊恐万状。为应变计,2月4日,南京行政院议决,政府迁都广州,并对关押在狱中的汉奸作出一项特殊规定:凡判处有期徒刑的,一律开释;判处无期的,转移台湾。然而尚未来得及转移,京沪杭战役打响。4月23日,南京解放。26日,全苏州监狱,除陈璧君等十几个无期徒刑者外,其他犯人均被释放,包括那些杀人犯、强盗、烟犯、汉奸等。当夜,蒋介石的城防司令又来电话说:“无期者亦可释放。”但不幸电话到监时,适典狱长李志锐已去朋友家住宿(自南京解放后,典狱长便不敢住在监里),根本不知有此电令,故也无从执行此令。迨至翌晨典狱长归来,人民解放军早已入城,并已接收了监狱。③就陈璧君而言,这确实是天大的“不幸”。人民解放军接收监狱后,陈璧君被移至公安局看守所约一个多月,又移送至司前街看守所。
原注:①朱子家:《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第三册。
②陈璧君在上海市监狱所写材料。
③陈璧君:《自白书》。
资料来源:
《从革命女志士到头号女汉奸——陈璧君传记》张静星著(1994年5月)